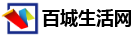50岁和80岁,一对单身母女同居养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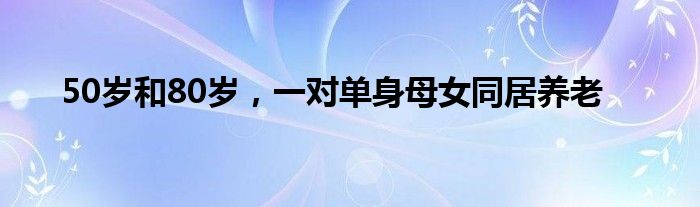
选择了一种特殊的养老安排:
在云南普洱的小屋里共同居住、生活。
20多年前,巫昂帮助妈妈逃离家暴的父亲,
她形容自己和妈妈、弟弟是一个“战团”,
一起开始了这个小家庭的“灾后重建”。
▲
巫昂和妈妈林秀莉在云南的家中阅读
巫昂说,“女儿应该天然地为母亲的观念和意识换血”。
同居第一年,
林秀莉就读了五六十本女儿推荐的书,
她喜欢一边做衣服,一边听播客,
吃早餐的时候雷打不动地上声乐课,
学手机摄影,自己修图、调色,
用手机操控一切智能家电。
现在,她已经成了同龄人中的影响力中心,
还想“学到100岁”,去宇宙旅行。
林秀莉经历过家暴的婚姻后,
从不催女儿结婚,女儿“想怎么样都同意”。
在她的支持之下,巫昂有了一张平静的书桌,
笔耕不缀地写作之外,也发展起了自己画画的事业。
在可供想象的母女关系里,
她们似乎提供了一种最和谐的样板——
她们不必一起吃饭、不共享同一作息,
甚至几天也说不上一句话,
但在相对独立的共处空间里,
她们知道彼此是相互支持、扶助的最小共同体。
自述:巫昂、林秀莉
编辑:金璐
责编:倪楚娇
巫昂和妈妈一起阅读,她们会一起讨论书中的内容、作者的生平
6月的普洱迎来了雨季,细细绵绵的凉雨会在每天下午降临,也是吃菌子和百根汤最好的时节。巫昂刚刚写完一个剧本大纲,到了可以暂时松一口气的阶段。
今年是巫昂和妈妈林秀莉两个人同住的第六年,也是在云南的第三年。2018年,因为家人生病,妈妈憔悴了许多,巫昂自己的身体也出了一些问题,于是她们果断地决定,搬到一起住。
▲
母女俩一起泡了姜片、青梅酒和杨梅酒
▲
巫昂和妈妈有各自独立的工作空间
这对母女相差30岁,共同点是,她们都单身。
50岁的巫昂,庆幸自己选择了不婚。她离开福建漳浦县城后,在复旦读文学,做过传统媒体的调查记者,但一直决定要“吃文学这碗饭”,离开机构媒体后,她将写小说作为自己一生的志业,这几年又开始画画,已经做了21年的自由职业。
80岁的林秀莉,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毕业后成了县城里有名的妇产科医生,28岁时和巫昂的父亲结了婚。当时她需要一边照顾家庭,一边照顾病人,“担子很重”,但与此同时,她还承受着丈夫不间断的家庭暴力,那二十几年里,没有唱歌跳舞的自由,不被允许穿好看的衣服,也没有人相信她说的话。直到55岁的时候,才在儿女的帮助下逃离她忍受了二十年家暴的婚姻。
艰难地剥离那个家之后,巫昂承诺过,要带妈妈一起生活。
▲
林秀莉为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食物
如今,她们真正地生活在了一起。她们的准则是,最大限度地为对方保留独立的空间。所有的时间里,她们几乎都在分头做自己的事情,有时候甚至很长时间说不上一句话。
在这个空间里,母女的称谓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巫昂和她的朋友们称妈妈为“林妹妹”,林妹妹则喜欢叫巫昂“巫老师”。
最近巫昂要做剧本,七八点就会起床。
而妈妈往往会睡到十点自然醒,然后开始做一顿蛋白质、碳水、纤维合理搭配的丰盛早餐,一边进食,一边听手机上的声乐课。她年轻时就很爱唱歌跳舞,但不好意思地跟我们说:“其实我不会唱啦现在,就听一听而已。”
林秀莉有时会在小区门口买点菜,回家后就开始一边做衣服,一边听播客和有声书,她最近喜欢听随机波动和爱丽丝·门罗。每次妈妈把做好的衣服发到群里,巫昂和弟弟、弟妹就疯狂鼓掌,还在母亲节的时候送了她一台缝纫机,所以她越干越有热情。
▲
最近林秀莉在为巫昂做新的衬衣
▲
林秀莉做衣服时,会认真地画出设计图纸、标明尺寸
林秀莉始终带着一股“理工科”的气质,她会为厨房的不同分区划定不同的专属抹布,做衣服的草图本上,也密密麻麻地画满了图和数字。
相比妈妈,巫昂则更加大条一些,但很好地遗传了妈妈年轻时对待工作的敬业精神,她从早到晚地沉浸在工作里,很容易听不见别人说话,直到傍晚,如果不下雨,她才会偶尔出门散步或是游泳。
她们在家务上有着顺其自然的分工。妈妈因为腿脚不方便,会多做一些洗衣、晾晒之类的工作,她在2011年就学会了网购,总是在网上买食材、零食和布料,也负责在网上交电费、水费,巫昂则更多负责跑腿的活儿:下楼取快递、扔垃圾、出门办事或采购。
一开始妈妈承担着更多的家务,但巫昂很快意识到了这不公平,于是开始非常有计划地削减家务,其中做饭明显是占用时间精力最多的,所以她们很早就解除了一起吃饭的绑定。
巫昂喜欢做米线,妈妈更喜欢一些蒸的粗粮和小面食,饮食习惯、进食时间有交集也有不同,就不必总是一起。
▲
在菜场买了气球准备回家
拍摄的第二天,巫昂和妈妈一起去菜场。她们会拉着手一起闲逛,像每一个新云南人一样好奇地询问那些菌子、药材的特性,巫昂也会在妈妈买肉的当儿,绕去另一边买米线。
巫昂买了一个兔子形状的卡通气球,系在小推车的把手上,妈妈拉着气球线开心地对着镜头笑。她们装满了一个小推车,满载而归,准备回家做春饼。
上野千鹤子在《始于极限》中说:“女儿是母亲最激烈的批判者,也是最狂热的拥护者。”但在巫昂和林秀莉身上,很少看到母女关系中常见的挣扎、冲突和张力,相反,她们正携手走在一条宁静、平和的重建路上,共同进步成了“更新版的自己”。
以下是她们的讲述。
▲
林秀莉抱着小时候的巫昂
林秀莉:
早年都是为了家庭的名声,外人看起来我们家庭特别好,他是中国科技大学,我福建医学院,两个孩子都上复旦。所以不管对方给我多少肉体上的侵犯,我都觉得说出去会影响到家庭的声誉,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都一直在压制内心的感受,强忍着不去跟他计较。
但是到后来,90年代末的时候,巫昂已经上研究生了,弟弟上了本科,首先是有了孩子给我的动力。巫昂跟我说,她亲眼看到她父亲打我以后,从小心里就有一个计划,她说跟他离了,以后跟弟弟带我上法院。
孩子发声以后,我觉得我应该摆脱这个人,不能再让他这样无端地伤害我。
当时他们家所有亲戚、兄弟姐妹都一起来反对,包括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同事、邻居,算起来大概有100个以上的人来跟我谈,劝我不要离。但我就觉得我不怕,我把我们给法院的诉讼还有孩子的意见书都给同事、朋友们看,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巫昂在意见书里写:“我从小就下定决心,在我有能力的时候要把我妈妈解救出来。”
▲
同居日子里,两人不会刻意非要一起吃饭
但我得到的支持太少了。第一次开庭那一天早上,我高中的七八个同学都跑到医院来,阻止我们去法院。我儿子对他们说,我妈妈挨打的时候你们都在哪里?我在还没有决定离婚之前,就给这些老同学们打过很多次电话,求他们帮我制止这个人的行为,但是他们有的人就说:“是真的吗?”觉得我在撒谎。
第一次开庭法院就判劝和,不同意离婚。但我那时候已经下定决心,我必须挣扎出来,当时的法律政策是两年分居就可以判离,我就坚持两年不理他。
以前他会干涉我所有的生活,好看的衣服、鞋子都不能穿,更不要说化妆。我很喜欢唱歌跳舞,但他强迫我退出了文宣队,一旦我的职位晋了级,他就脸色不好,不跟我一起走,为什么他那么恨我我也不知道。
离婚之后,我就想自由了。我想要穿上我喜欢的衣服,跟其他人一样,化妆打扮,自由地去唱歌跳舞。
▲
早年巫昂和妈妈一起出游的合照
巫昂:
从我记事以后,父亲的家暴是没有间断过的,他随时都会发怒,我妈非常不容易,她的身体受到很多伤害。
我也是最近因为开始写一些关于我父母婚姻的文章,才去问我妈一些问题,以前我根本不敢问,比如她的膝盖是怎么回事,她说是我父亲有一次从后面顶她的膝盖,因为她个子很小,不到1米5,就直接跪在了地上,她的半月板就碎了,这直接影响了她整个后半生的生活品质,现在她也没办法走很长的路。
我作为她的女儿,其实只是一个目击证人而已。真正的痛苦是在她的人生如此黄金的二十几年里,都在忍受这段婚姻。
我们当时其实真的是“逃离”,趁着我爸去上班的时间,先让她人逃出来,我弟和我小姨是内应,帮她把东西收拾好,约了司机,从那个家里搬出来,到我妈医院的医生值班室去住。
我妈完全是净身出户。后来我们调侃那个家是我们的“沦陷区”,小时候很宝贵的童年记忆都没来得及解救出来,有时候会突然想起来我们的集邮簿、《一千零一夜》都还在“沦陷区”。
▲
如今安宁的生活,是曾经艰难的挣扎和反抗换来的
巫昂说:“只有亲历了这一切才知道当下的生活有多珍贵”
我写诗的时候非常直接地写过很多这样的经历。在我写了逃离家暴后和母亲同居的文章后,很多的女孩小窗告诉我,自己的家庭也是这样的。我觉得大家不应该回到家承受这样的恐惧、暴力和痛苦,就好像你生活在战乱区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个责任让她们知道说,这条路你是可以走通的,可以走得很安全、很好,可以靠你自己过上一种很安宁的生活。
我曾经想过我妈妈可能在婚姻里是活不到60岁的,但是她现在已经80了,我们为她、她自己也为自己争取到了离婚后这么平安快乐的生活。
▲
巫昂会为家里定期换上当季的本地鲜花
林秀莉:
我们一起住的第一年,我看了五六十本书。巫昂给我推荐了很多书,她会想我适合看什么书,比如杨绛、汪曾祺、余华、苏童这些,然后一批批地拿来。
后来第二年我就觉得,不能这样老闲着,应该找个什么事干。我小时候经常帮妈妈缝纽扣洞,当时就觉得能亲手做出衣服穿在自己身上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但后来工作以后一直没时间做。
▲
退休以后,林秀莉如愿开始做衣服
2011年她就学会了用手机网购,家里的布料都是她自己在直播间抢的
所以我就想何不买点布料,这些网上都可以买到,就这样慢慢地开始学起来了。这出自我个人的爱好,后来给孩子做衣服的几年过程里,我自己也感觉有点进步,我给孩子做的衣服,他们都没嫌弃,还穿到公众场合去,我就更有兴趣了。
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件衣服是我做的双面羊绒大衣,这几年也在尝试做一些男装。
▲
林秀莉练习手机摄影
去年我还上了手机摄影课,学了一个月,粗粗地摸了一点门道。我的腿没办法到处走,就在小区里逛逛拍拍。这里的树长得很高,那天我看到有一棵树有六层楼那么高,就想我要把它拍下来。然后等明年再拍一次,那时候可能会长到七层楼了。
而且现在家居都是智能化的,如果我不懂这些的话,就应付不了生活。你看现在家里的电饭煲、扫地机我都是用手机来控制的。
▲
家里的各个地方都挂上了巫昂自己的画
巫昂:
我觉得女儿天然地应该为母亲的观念和意识,特别是女性主义的观念和意识换血。
妈妈并不是说不想,或是没有能力变成2.0、3.0版本的自己,只是她所处的时代没有利于女性发展的土壤。如果你自己不学习,你就没有能力为她去换血。
中国人以前是有点不愿意直面敏感问题的,比如对女人的处境、婚育的选择,甚至搞钱这种事情都有点害羞。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羞愧的,你就应该把它们放在桌面上,像男人一样去讨论。
▲
林秀莉给儿子做的男士衬衫,和店里卖的别无二致
很多人说,对母亲进行教育和感染的进度是很慢的,甚至有很多反复,过一阵又复发了之类的,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
你可以在她的五感能触及到的地方,非常“有心机”地布置一些你的教材。比如说我很喜欢买好看的器物回家,但一开始我妈就会说怎么看都是灰灰的,像洗不干净一样,等到我搞艺术的朋友来我家吃饭,他们疯狂拍照,一直夸,我妈就突然顿悟了,意识到原来这是美的。
你要给她时间,因为她们这几代人没怎么接触过审美性的教育,或者更先锋、更有灰度的人生。你要给她一些点对点的指导,比如转发一些有营养的链接,使她知道世界上有些人不是那么传统地活着,年轻人有很多不同的活法,但它依然是可行的,我的女儿也可以过得很幸福。
另外,你要让妈妈知道你的经济状况,如果她知道你口袋里有钱,她就不会特别担忧。
我妈现在已经成为她前后两三代人的一个新的影响力中心,她整个人都更新了一版。
她会非常主动地把我传播给她的东西告诉她的同事、同学、晚辈,教育他们不要催婚孩子,打电话给她那些不思进取的老年亲戚说你们应该去听播客,要学会网购,要学习使用APP。
这几年,巫昂在写作之外探索了画画这一第二职业,还举办了个展
巫昂:
我肯定跟所有的70后一样,也纠结过、尝试过想要建立亲密关系。我妈妈的故事给了我很多警示和思考的机会。
有的同学老是跟我说,“女人最大的价值、最终的归宿就是婚姻”,对这种陈词滥调我是毫不留情的。他们的下一招就是说“你搞文学也没挣到什么钱”,我说:“你怎么知道?”
我和妈妈也有过非常开诚布公的交流,我妈妈的观点甚至比90后还要前卫,所以她也从来不会催婚的。
▲
巫昂画的基本都是女性
我妈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优点:她觉得她的孩子不管做任何选择都是有道理的,她坚信我们是对的。她不以金钱来衡量我的成功或者失败,而是以我是否发挥到自己最应该发挥的能力作为恒定的标准。
所以哪怕我在当时那个年代,选择离开媒体高薪的职位,出来一下子进入到千字30-50块钱的小说行业,我妈也觉得无可厚非,这种支持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已经做自由职业21年了,这几年我又开始画画,有了一个第二职业。我每做一件事,都力求能够用我全部的热情,全部的专注度去完成它。我妈妈会很支持我所有这些哪怕不重要的选择。
▲
巫昂工作室的墙上贴满了文学相关的便签,写着世界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和年代;客厅和画室的书柜里都堆满了书
林秀莉:
我在上医学院的时候,当时婚姻根本没有什么标准,我也没有特别爱谁,到最后自己都决定不了。当时有五六个人给我写信,我拿去问我的表姐,她看了看说这个人是名牌大学的,就这个好了。你看我们当时处对象是这样选的。
现在巫昂她这么努力地在做每一件事,我就感觉她快乐就好。她想怎么样我真的都同意,我不会怕以后没有后代来给她养老,我觉得社会在进步,以后的社会服务都会跟得上这些不婚不育的人。
▲
林秀莉翻阅自己的服装设计册
巫昂:
和妈妈一起生活,最重要的是让我至少拥有了几年平静的书桌。因为我们相互的支持,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完全不考虑挣钱的问题,我从前几年那种铁血战士的状态里放松下来了,就安心地发展我的第二事业。
因为我要带着妈妈,又是自由职业,所以不能太晚考虑养老这件事,我40岁就开始有意识了。我和弟弟、弟妹都很团结,我们就像一个军团,非常有规划,我们思考解决方案都跟当年带妈妈逃离是一种战斗风格。
▲
母女俩在菜场分头采购,妈妈会使用手机支付买菜
我跟妈妈交流之后,首先我们都决定是不会送她去养老院的,像上野千鹤子老师说的,“在家中离世”,我觉得很好。我和我母亲都是不想要坟地的,觉得会增加没有必要的负担。遗嘱她很早就处理好了,我们也会直面遗嘱公证,这都没有什么好避讳和羞愧的。
我们在普洱思茅这边也有意识地结交了一些当地的朋友,万一我去出差,也有人能够随时过来,如果有必要有一天我们也会请保姆或者护工。
已经在社会上经历过这么多风雨的人,为什么要在养老面前止步不前或恐惧?为什么要害怕死亡?我觉得对于死亡的理性是一个在生活中搏斗过的人应有的一种选择。
▲
在菜场买肉和气球
林秀莉:
人老在生理上是一种自然规律,器官衰退,这个都是正常的。人要正视年龄的增加和身体的退化,不要因为衰老悲观丧气。
我觉得我必须要像年轻人一样要充满活力,所以我常常会想不起今年几岁,老是会记不住。
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两个人。一个是杨绛,她是我最尊崇的楷模。看了好多本她的书以后,我在她身上得到很大的前行的力量。她女儿去世,我说她怎么撑得住,巫昂就会跟我说杨绛是一个怎样的人。她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但一直到100岁以后还在工作,还在写作。
另一个是盲人歌手周云蓬,我非常喜欢他。他9岁就失明,但还是一直上到大学,写作、创作、写民谣,还到处去巡演,前年血压都升高了,他照样没有停息过。我曾经问他,你这个力量是哪里来的?他给我说,你什么都不要想。
▲
林秀莉每天在网上听声乐课
所以我有什么可以总是七想八想、停滞不前的理由呢?我也必须像他们一样,如果我能活到100岁,我也要学到100岁。
我只想跟上时代,未来我要多学一些人工智能这方面的知识。人家现在不是说以后会有宇宙旅行吗?我总是跟我的老同事们说,要好好活着,以后一起去住太空酒店。有那么一天,我也想登上宇宙飞船去遨游整个大宇宙,去亲眼目睹一下宇宙间的星球。
免责声明:本文由用户上传,与本网站立场无关。财经信息仅供读者参考,并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江淮iEV7试驾预约流程如下:首先,访问江淮汽车官网或关注官方公众号,进入“试驾预约”页面。填写个人信息,...浏览全文>>
-
试驾MG4 EV全攻略:MG4 EV是一款主打年轻科技感的纯电紧凑型车,外观时尚,内饰简洁。试驾时重点关注其动力...浏览全文>>
-
预约试驾奥迪SQ5 Sportback,线上+线下操作指南如下:线上预约:访问奥迪官网或官方App,选择“试驾预约”,...浏览全文>>
-
试驾别克君越,一键启动,开启豪华驾驶之旅。作为一款中大型轿车,君越以优雅外观、舒适空间和强劲动力赢得广...浏览全文>>
-
试驾沃尔沃XC40时,需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提前预约试驾时间,确保车辆状态良好。其次,熟悉车辆智能安全系统...浏览全文>>
-
预约宝马X1试驾前,建议提前通过官网或电话联系4S店,确认车型库存与试驾时间。到店后,先与销售顾问沟通需求...浏览全文>>
-
比亚迪海豹05 DM-i试驾预约流程如下:首先,访问比亚迪官网或关注官方公众号,进入“试驾预约”页面。填写个...浏览全文>>
-
试驾奇骏时,建议关注以下几点:首先,提前预约专业试驾路线,熟悉车辆性能;其次,注意检查车辆外观及内饰是...浏览全文>>
-
凯迪拉克CT5预约试驾,从线上到线下,体验顺畅而专业。只需几步简单操作,即可在官网或App上选择心仪门店与时...浏览全文>>
-
预约东风富康试驾可通过以下步骤进行:1 官网或官方App:访问东风富康官网或下载其官方App,进入“试驾预约...浏览全文>>
- 比亚迪海豹05DM-i试驾预约流程
- 云度新能源预约试驾有哪些途径
- 阿维塔07试驾预约,体验极致驾驶乐趣
- 宾利试驾,快速操作,轻松体验驾驶乐趣
- 全顺试驾预约,一键搞定,开启豪华驾驶之旅
- QQ多米试驾预约,轻松搞定试驾
- 零跑C10试驾的流程是什么
- 宝马X1预约试驾,4S店体验全攻略
- 试驾QQ多米,畅享豪华驾乘,体验卓越性能
- 江铃集团新能源试驾预约,一键搞定,开启豪华驾驶之旅
- 试驾雷克萨斯ES如何快速锁定试驾名额?
- 兰博基尼试驾预约有哪些途径
- 试驾五菱凯捷有哪些途径
- 力帆预约试驾,一键搞定,开启豪华驾驶之旅
- 极石汽车试驾预约,4S店体验全攻略
- 本田雅阁试驾,新手试驾注意事项
- 捷途旅行者试驾预约预约流程
- 昊铂试驾预约,快速通道开启豪华体验
- 五菱预约试驾,开启完美驾驭之旅
- 试驾捷豹E-PACE,4S店体验全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