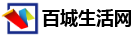逃到鹤岗的年轻人,逃回了北京

去鹤岗的人和 " 逃离北上广,裸辞去大理 " 的数字游民不一样。在大理,总有流动的酒吧派对、社区分享、聊天随时展开,又随时结束。选择大理的人也许想摆脱一线城市沉重的社交负担,可总还是期待着与他人建立联结。
而在鹤岗,人们表现出隔绝一切的决心。" 喝奶茶会让我开心,靠垫能让我靠着舒适,猫能为我做它们所有能做的事情,但人不能。和人交往有什么用?" 林雯曾这样说过。两人走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鹤岗街头,李颖迪试探地问:" 但你一个人会不会 ……" 话没说完,对方马上摇头:不会。好像已经无数次说服过自己:我不会孤独。
作者 | 陈茁编辑 | 钟毅题图 | 《去有风的地方》
2022 年 10 月,李颖迪带着一件短款羽绒衣和两件毛衣来到了正处于话题中心的鹤岗。
就在李颖迪启程前,一条 " 女子逃离大城市去鹤岗全款一万五千元买房 " 的新闻再次点燃了互联网对鹤岗的热议。
资源枯竭、房价洼地、躺平天堂,过去三年间," 隐居吧 " 的关注者从 55 万涨到接近 140 万," 隐士 " 们在吧里互相推荐隐居地:河南鹤壁、安徽淮南、山东乳山 …… 还有俨然已成为某种符号化存在的东北鹤岗。
(图 /《走走停停》)
花北上广一平米房价的钱,就能在此拥有一套四十平米的房,过上向往的隐居生活,鹤岗是抚平当代年轻人倦怠情绪的精神乌托邦,一种即时可得的自由代餐。
逃跑吧,上路吧。
我们在网上窥视他人的隐居生活,幻想一场奋不顾身的逃离,把拥挤的早高峰、绩效 KPI 和令人疲惫的人际关系全部抛之脑后,然后继续忍受日复一日的生活,想走又不敢走。
" 出走后,人们真的能得到期许中的自由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李颖迪来到鹤岗,尝试了一次为期三个月的 " 逃跑实验 "。但直到写完《逃走的人》,她依旧没有找到答案。
(图 /《我在他乡挺好的》)
在鹤岗的冬天,她分外想念北京的朋友们,与此同时,她也看见 " 浪漫化 " 的逃离背后,自我隔绝可能的代价。
新书发布后,书中的一位受访者告诉李颖迪,他已经结束蛰居状态,回老家了。李颖迪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李颖迪也回到了原本的生活轨道,在北京继续写作。她仍时不时地涌起逃离的冲动,但她也逐渐接受,也许有一类人,就像伯恩哈德所说的 " 不能忍受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有在他们需要离开和正在要去的地方之间,他们才是幸福的 "。
《逃走的人》作者 : 李颖迪 出版社 : 新经典|文汇出版社 2024-8
一路向北,去鹤岗
如果将中国地图看作一只公鸡,北纬 47° 附近的鹤岗恰好长在公鸡脖颈处,再往北不远就是俄罗斯。这是一座 " 与雪共生的城市 ",全年平均气温不到 5 ℃,每到冬天,白昼短得仿佛一场梦。
出发去鹤岗前,李颖迪曾与热搜词条中的主人公通过一次电话。在电话一端,她想象着这个 1996 年出生的女孩所描述的生活:每天中午从纯白的北欧风家中醒来,一个人下厨、吃饭、打扫卫生,在五只猫的陪伴下画画赚钱,每个月出门散步一次,已经几年没和人见面。
这也是两人唯一一次对话,舆论喧嚣之下,女孩像受惊的动物,迅速躲回地下洞穴。
" 消失 " 在鹤岗时常发生。微信群聊几乎每分钟都有人说话,现实生活中却见不到人。所有人以网名称呼彼此,一个人会毫无征兆地消失,约好一起吃饭,然后再也没有出现。
(图 /《没有工作的一年》)
在鹤岗的头两个星期,李颖迪见得最多的,是找不到采访对象的同行。没有人愿意出来说话,毕竟他们来鹤岗的初衷就是想隐姓埋名。尤其是在彼时彼刻,外界的关注带来警惕和不耐。
李颖迪并非完全以记者的身份来到鹤岗,从一开始,她就打算在这儿住一段日子。住在鹤岗的人,就像一个个紧闭的蚌壳,只有通过时间,蚌壳才会慢慢张开,你才会看到里面真实的样貌。
2021 年,她写了一篇关于 " 隐居吧 " 的报道,在另一些常被谈起的隐居地——河南鹤壁、安徽淮南、山东乳山 " 旁观 " 了几个年轻男性的生活。34 岁的王浩,从郑州富士康的流水线上逃走,离开朝不保夕的生活,花五万块在鹤壁买了一套六十平米的房。
(图 /《我在他乡挺好的》)
还有 27 岁的杨亮,辗转于上海各种零工岗位之间,却迟迟看不到上升的希望。原本打算攒到 30 万就辞职隐居,但和领导的某次冲突使得计划提前。2020 年冬天,他辞去干了三年的保安工作,跑到鹤壁,花 3.7 万元买下一套接近毛坯的两室一厅。
但李颖迪翻遍几百人的鹤壁群,只找到两个女生,还都只是加群先打听看看。她问王浩和杨亮,来这儿的到底有没有女生,答案都是没有。
鹤岗则不一样。当地房产中介告诉李颖迪,这两年,在鹤岗买房的女性已超过总人数的一半。说实话,李颖迪也有些心动。
中介给李颖迪推荐了一套三万的房。(图 / 受访者供图)
她在一间 1500 元包月的民宿住下,等待隔离结束,又搬到南边的回迁小区九州松鹤。小区內楼房密集,胜在交通便利,附近餐厅、超市一应俱全。李颖迪租下的开间在四楼,没有电梯," 墙壁很薄,不时传来过路人的脚步声。"
买房是件大事,她想先试试,能不能像那些只身前去鹤岗的女生一样," 隐居 " 一阵子。
最初,《逃走的人》定下的书名是《隐居者》,也有人提议过叫《隐居一代》,李颖迪觉得这个词 " 太大 " ——她无法像社会学者那样从理论上创造一个新概念,也不愿用宏大的词语去定义这群人," 隐居者、避世者、躺平的人、逃走的人、躲起来的人 ",都不够准确。
似乎只能用否定式的描述让他们的面貌浮现出来。他们绝不是陶渊明般田园牧歌式的隐居者,也并非梭罗那样远离城市,栖居在瓦尔登湖畔的自然主义者。水电网、外卖和快递仍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品。
与依靠日结工资生存的三和大神不同,逃向这些资源枯竭城市的隐居者虽算不上经济富裕,但基本都有一定积蓄,其中还有不少人收入可观。
(图 /《没有工作的一年》)
李颖迪书中的主角之一林雯一口气在鹤岗买下两套房,一套自住,一套开炸串店,每天卖七八单,就能实现 " 有限度的自由 "。
可他们又和 " 逃离北上广,裸辞去大理 " 的数字游民不一样。在大理,总有流动的酒吧派对、社区分享、聊天随时展开,又随时结束。选择大理的人也许想摆脱一线城市沉重的社交负担,可总还是期待着与他人建立联结。
然而在鹤岗,人们表现出隔绝一切的决心。" 喝奶茶会让我开心,靠垫能让我靠着舒适,猫能为我做它们所有能做的事情,但人不能。和人交往有什么用?" 林雯曾这样说过。两人走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鹤岗街头,李颖迪试探地问:" 但你一个人会不会 ……" 话没说完,对方马上摇头:不会。好像已经无数次说服过自己:我不会孤独。
一定要说的话,他们与日本蛰居族——一群不上学、不工作、不社交,几乎不走出家门甚至房门的隐居青年——有不少类似之处,区别是日本蛰居族往往与父母同住,而对逃向鹤岗的青年们而言,家庭本就是他们想要逃离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图 / 受访者供图)
逃离一切,然后呢?
从某种程度来说,去鹤岗,也是李颖迪 " 蓄谋已久 " 的一次逃离实验。书写《逃走的人》,则是对她本身生活境况的回应。
2022 年秋天,新冠尚未结束,生活仿佛一根拉到极限的皮筋,没人知道何时会崩断。李颖迪待在北京的屋子里漫无目的地刷新闻,故事里的女孩把旧房改造得焕然一新,让她想起几乎快被遗忘的动森小岛。有半年时间,她每天泡在《动物森友会》里,种地、捡树枝、盖房子、收集奇形怪状的恐龙化石,像布置现实生活中的家一样,在虚拟世界 " 编织精神飞地 "。
如今回想起来,那是李颖迪二十多年人生中格外灰暗的一段。从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她顺利进入一家业内顶尖的时尚杂志社,期许着写出 " 这个时代最好的一批稿子 "。未曾想工作不到一年,公司发生人事震荡,整个编辑部四分五裂,学生时期尊敬的 " 职业标杆 " 跌落神坛,曾经并肩作战的同事形同陌路。
(图 /《突如其来的假期》)
她突然意识到,原来人的话语背后存在如此多潜台词。工作、人际关系,无不令她幻灭," 人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 "。身体最为诚实——她辞了职,回退到小小的房间,不看微信,很少出门,漂在网上逛 " 家里蹲自救同盟 ",到处搜索代缴五险一金。
那阵子,她总是想起卡佛笔下一个失业的男人。美国大萧条期间,男人被公司解雇,从此就耗在沙发上,除了每两周出门签字领失业救济金,再也起不来了。李颖迪坐在桌前,看着窗外的天色一点点变得晦暗,她害怕自己也会像那个男人一样,困在房子里再也出不去了。
人必须努力变强,才能脱离困境,获得成功,改变命运。18 岁以前接受的教育铿锵有力,一声声催促李颖迪把自己拔起来。于是,她穿上衣柜里最正式的连衣裙,化好妆,背着电脑到咖啡馆假装工作,无所事事。
(图 /《突如其来的假期》)
《1818 黄金眼》的一条搞笑新闻吸引了她的目光:一个男人为了逃避上班躲在家里,没想到妻子突然回家,情急之下便反锁大门躲进了衣柜,把自己藏在衣物堆里。
" 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躲起来。" 袁哲生在《寂寞的游戏》里写,人天生就喜欢躲藏,渴望消失,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事。2019 年,李颖迪第一次关注到 " 鹤岗白菜价买房 " 的新闻。经历了失业、疫情,倦怠情绪从一小撮人,逐渐蔓延到整个社会。她明白这不止关于鹤岗一座城市,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 当我们对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外部世界感到无能为力,你就不想干了,你就想逃了。"
李颖迪在鹤岗北山公园。(图 / 受访者供图)
逃离,一直是贯穿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一个人从既定的生活轨迹中逃离,游走在世俗陈规和真实的欲望之间,如《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苦闷孤独的霍尔顿,《玩偶之家》里从家庭出走的娜拉,艾丽丝 · 门罗笔下一次次逃离而又逃无可逃的主角 ……
回到现实中,当我们用 " 逃 " 讲述一个故事,听上去总带有某种不赞同与批判。我们说一个人 " 当逃兵 "" 临阵脱逃 "" 落荒而逃 ",所有这些表达都暗示了一种普遍的看法,即 " 逃 " 是懦弱、可耻的失败者行为。
最初接触杨亮等人时,李颖迪也将他们的 " 逃 " 归因于社会化不顺利导致的被动选择。后来,她跟着林雯回到林雯的常州老家,见到客厅沙发上沉默寡言的男人和又一次发来相亲对象照片的林雯妈妈。她去到林雯曾经工作的手机回收公司,隔着玻璃门,想象林雯在滴滴作响的倒计时下,不断敲击键盘的声音。
越走近他们的生活,李颖迪反而理解,逃也可以是一种主动行为,一个正在进行的动作。为了躲避工作、家庭、社交关系,拒绝所有旧秩序下的规则和期待,逃走的人付出代价和勇气,主动追求全新的生活。他们没有放弃自我,恰恰相反,逃走是他们寻找自我的起点。
" 真正被动的也许是我们这些还在工作、还在忍受的人。" 李颖迪自嘲,但她也忍不住想,逃跑之后呢?人真的就能获得梦寐以求的自由了吗?
" 问题的解药在关系里 "
从林雯那儿,李颖迪第一次听说了大西洋海刺水母。她给李颖迪看自己养的水母照片——这是她在鹤岗的新爱好——两只透明的 " 大西洋 " 漂在价格不菲的 " 月光水母缸 " 里,彩色的灯打下来,美好得就像林雯崭新的生活。
后来,在林雯鹤岗的房子里,李颖迪提出想看一看 " 大西洋 ",却得知它们不吃饭饿死了。林雯看着水母的身体越来越小,直到有一天,彻底溶化在水里,没了踪影。李颖迪请朋友把它画在《逃走的人》封面上,伞体接近透明,触须悠长而梦幻,和鹤岗的生活一样,呈现出消失的气质。
鹤岗为数不多的娱乐生活:三家酒吧、两家剧本杀店。(图 / 受访者供图)
艾丽丝 · 门罗写,逃离,或许是旧的结束,或许是新的开始,或许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瞬间,就像看戏路上放松的脚步,就像午后窗边怅然的向往。
没人想过,逃离的结局,也可能是大西洋水母一般的消失。
牵住李颖迪的是来自他人的关心和爱。她也一度以为人生可以不需要朋友,不需要亲密关系,不需要来自家庭的支撑。但在鹤岗的那个冬天,几十个独自熬过的黑夜,令她分外想念北京的朋友们。她写信给好友,说感觉整个人像在水里,不断下坠;只要出门,身上就冷得发疼,走在鹤岗空旷的街头,眼前只有雪,一个人都没有。
白雪笼罩的鹤岗。(图 / 受访者供图)
失望也好,苦涩也罢," 人可能就是要忍受现实生活带来的挫败感 ",再一次尝试与世界相连。李颖迪逐渐懂得,我们只能练习接受这件事:逃离并非生活的终点。
从审美上,她依然理解、相信逃离所蕴含的价值,逃离的念头也时常在她的脑海中徘徊。她好几次提起一个从大厂离职就没再长期工作的朋友。最近,这个朋友在北欧打工旅行,修船、刷墙、造房子、在牧场捡羊粪便," 我还是希望去一个遥远的地方,过向往的生活。"
但她也学着不再用浪漫化的眼光看待 " 逃离 "。面对辞职回长沙躺平、逐渐失联的朋友,她会劝说,咱们再试一试,再回来尽力找份工作,再 " 忍受 " 一段时间试试看。鹤岗的日子让她明白,隔绝自我的生活不一定会通向自由,也可能是难以承受的全然失控。
大雪之后,李颖迪独自一人。(图 / 受访者供图)
写下来,她就存在了
眼下,能让李颖迪坚持 " 忍受 " 的便是阅读和写作。
从鹤岗回到北京后,心理咨询又持续了两三个月。直到有一次,李颖迪跟咨询师说,还是想试试通过写作解决自己的困惑和痛苦。就像第一次辞职时,李颖迪写了一篇文章回溯整个职场事件中的经历," 写下来我就没那么痛苦了,好像我把它封住了,变成了一颗琥珀,它就可以离开我了。" 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人可以通过写作实现一部分精神上的自由。
写《逃走的人》于她而言,也像封存一颗琥珀。原本的计划,只是把过去几年发表的相关报道结集成册。写着写着,李颖迪和编辑都认为,有必要加入更多她在鹤岗的经历和感受,用她的视角寻找逃走的人,也是在寻找她自己。
(图 /《去有风的地方》)
书出版后,有人给李颖迪发邮件,说她写出了当下共同的处境。北漂和鹤漂,没有太大区别;金台夕照的国贸 CBD 和工厂流水线前,人同样渺小无力。
也有读者批评书 " 写得太浅显 "" 没有带来新的启发 "。李颖迪理解的 " 浅显 ",是她没能像学者创作非虚构作品那样,给出明晰的理解框架和强有力的判断。采访中,她也习惯性地用 " 具体经验 " 来回复,细致地回忆环境、话语以及她的感受。
李颖迪明白人们对解释的渴求,她也是如此。为了回答 " 爱的能力为什么越来越稀缺 ",她开始阅读哲学,韩炳哲的《爱欲之死》勾连出弗洛姆的《爱的艺术》和《逃避自由》,又把她引向叔本华。
《人生的智慧》作者 : [ 德 ] 叔本华译者 : 韦启昌出版社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4
最近,她刚刚读完《人生的智慧》,这位 " 悲观主义哲学家 " 在书里写:人生不存在幸福,应抛弃对幸福的迷思,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尽力去避免灾祸的发生。意识到自己的痛苦早在几百年前就有人思考过,还给出了 " 一些可能的答案 ",她感到被轻轻抚慰,读到共鸣之处,便认真记下。
但李颖迪坦言,她没法给出答案。相比理念,她更倾向于在写作中呈现经验本身——那些生活中复杂的、难以像新闻标题一样用一句话概括的内容。" 语言的准确是最重要的 "。生活无法用一句话总结,文学也是如此。
人类学学者袁长庚评价李颖迪的写作," 不因其不可置疑的道德优越性而板起脸来教训人。相反,他人是作者散落于人间的无数镜像。颖迪的文字和她笔下的人物一样,有一种让人心动的朴拙和踟蹰。"
这种踟蹰来自于,当她回看以前的报道,发现很多判断下得都非常粗浅,容易被推翻。"(写得)太快了,还是太快了。" 李颖迪感到对新闻的兴趣正在慢慢消退," 我只想尊重我的经验和感受,尊重这些人的经验和感受。" 她形容心目中好的写作,就像海明威战后写迷惘的一代,不分析,不评判,只是诚实地写下他们的生存状态和虚无的感受。
(图 /《何时是读书天》)
非虚构以外,李颖迪 " 也在试着写小说 ",作家的第一本书,往往隐藏着他持续关注一生的命题。李颖迪笔下的故事大多仍围绕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一次,离她自己的生活更近。
说试着,是因为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小说写得如何,或者说并不清楚小说到底该怎么写。但只要写下来,她就高兴了,她就存在了。文字是最好的咨询师,在写作的私人花园里,她卸下武装,完全自由。
免责声明:本文由用户上传,与本网站立场无关。财经信息仅供读者参考,并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江淮iEV7试驾预约流程如下:首先,访问江淮汽车官网或关注官方公众号,进入“试驾预约”页面。填写个人信息,...浏览全文>>
-
试驾MG4 EV全攻略:MG4 EV是一款主打年轻科技感的纯电紧凑型车,外观时尚,内饰简洁。试驾时重点关注其动力...浏览全文>>
-
预约试驾奥迪SQ5 Sportback,线上+线下操作指南如下:线上预约:访问奥迪官网或官方App,选择“试驾预约”,...浏览全文>>
-
试驾别克君越,一键启动,开启豪华驾驶之旅。作为一款中大型轿车,君越以优雅外观、舒适空间和强劲动力赢得广...浏览全文>>
-
试驾沃尔沃XC40时,需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提前预约试驾时间,确保车辆状态良好。其次,熟悉车辆智能安全系统...浏览全文>>
-
预约宝马X1试驾前,建议提前通过官网或电话联系4S店,确认车型库存与试驾时间。到店后,先与销售顾问沟通需求...浏览全文>>
-
比亚迪海豹05 DM-i试驾预约流程如下:首先,访问比亚迪官网或关注官方公众号,进入“试驾预约”页面。填写个...浏览全文>>
-
试驾奇骏时,建议关注以下几点:首先,提前预约专业试驾路线,熟悉车辆性能;其次,注意检查车辆外观及内饰是...浏览全文>>
-
凯迪拉克CT5预约试驾,从线上到线下,体验顺畅而专业。只需几步简单操作,即可在官网或App上选择心仪门店与时...浏览全文>>
-
预约东风富康试驾可通过以下步骤进行:1 官网或官方App:访问东风富康官网或下载其官方App,进入“试驾预约...浏览全文>>
- 比亚迪海豹05DM-i试驾预约流程
- 云度新能源预约试驾有哪些途径
- 阿维塔07试驾预约,体验极致驾驶乐趣
- 宾利试驾,快速操作,轻松体验驾驶乐趣
- 全顺试驾预约,一键搞定,开启豪华驾驶之旅
- QQ多米试驾预约,轻松搞定试驾
- 零跑C10试驾的流程是什么
- 宝马X1预约试驾,4S店体验全攻略
- 试驾QQ多米,畅享豪华驾乘,体验卓越性能
- 江铃集团新能源试驾预约,一键搞定,开启豪华驾驶之旅
- 试驾雷克萨斯ES如何快速锁定试驾名额?
- 兰博基尼试驾预约有哪些途径
- 试驾五菱凯捷有哪些途径
- 力帆预约试驾,一键搞定,开启豪华驾驶之旅
- 极石汽车试驾预约,4S店体验全攻略
- 本田雅阁试驾,新手试驾注意事项
- 捷途旅行者试驾预约预约流程
- 昊铂试驾预约,快速通道开启豪华体验
- 五菱预约试驾,开启完美驾驭之旅
- 试驾捷豹E-PACE,4S店体验全攻略